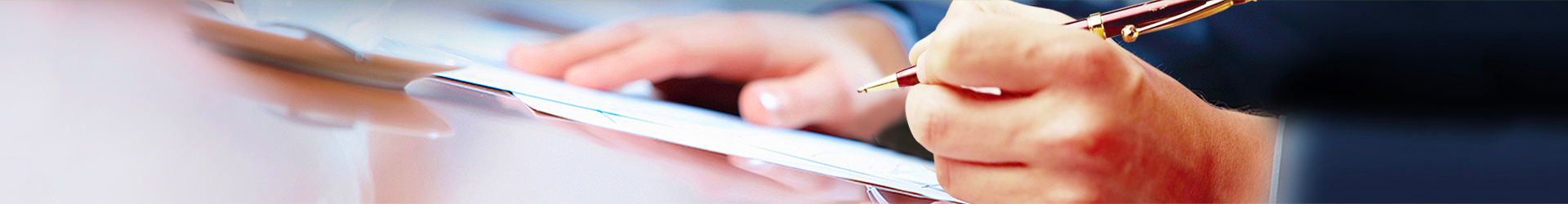
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一、《保护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的通过带来的机遇
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这是继2001年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之后,教科文组织在保护全球文化多样性方面做出的新的努力;它也反映出在世纪之初,当文化发展与市场扩张发生深度碰撞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做出的抉择。应该说,这一国际法文件的通过是人类史进入21世纪后的一个重大事件。
文化多样性不仅是一种文化现实,也是一个价值选择。保护文化多样性意味着人类各民族愿为长久地维护不同民族带有极大差异的文化表达形式的丰饶性而付出艰辛的努力。同时,《公约》也不仅像《宣言》那样仅仅停留在道德原则的呼吁上,而是要将保护行动落实到现实生活与市场交往当中去。《公约》对民族国家以政策工具推动境内文化多样性发展,以及本国文化产品市场竞争力提高的主权权利予以明确认定。对同时具有价值和商品两种属性的文化产品的市场交易准则予以特殊的强调。《公约》的通过和不久后的生效将引起整个国际法体系的一系列调整。《公约》的通过也将对一些国家内部的文化发展战略与政策走向发生特定的影响。
由于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同一部国际法文件对他们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公约》对不同国家的意义有两种情况。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或发达国家集团而言,这种国际政策工具将得到实实在在的运用,其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将得到有效的激励,获得较大的市场空间;而众多发展中国家从这一《公约》得到的主要是一种道义的支持。当然,这两种情况之间并没有截然的阻隔,从中获益多少主要是与各国的发展程度及转型进程呈正相关。
中国在所有支持这部国际公约通过的国家中处于一个较为特殊的地位。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将中国送上了在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向发达国家迈进的征程。这个进程同时也要求中国经济经过复杂而精微的调整,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走上与社会、文化、生态和谐发展的道路。这时迅速发展起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几乎是他无二的选择。这将是一个靠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来有效推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与国际环境不断互动的进程。《公约》的通过给他这一战略调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靠着政策工具的正确使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将面对较轻的国际文化贸易压力,将借助极具潜力的国内市场的开发使自己羽翼丰满。否则他也可能再次失去历史机遇,而我们本来已不太缺少道义的支持。
二、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是把握住历史机遇的必要条件
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有赖于我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壮大。《公约》这一历史机遇的出现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是紧迫感而不仅是安全感、放心感。文化产业发达如法国、加拿大尚且倾全力推动《公约》的制定,可见文化市场对于21世纪民族国家的健康发展何等重要。
更具体地说,我们“入世”时已经作出过不少承诺。这些承诺对于国内文化产业分量已相当沉重。例如说每年20部影片的引进,我们可以设想,即使像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与文化市场,每年真正可以吸引人进入电影院的影片能有几部呢?我们现在已能吸引足够观众的电影每年有了几部呢?!此外,国内那些自然人文景观、文物及文化遗址在支撑我们旅游业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在同等速率地耗损、衰竭,如没有强大的内容原创能力的崛起和新产品源源不断地面世,我们的文化产业发展又怎可持续?!
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我们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举步维艰,我们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市场是那样雕敝。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和坦承的现实。而之所以会如此,文化生产与提供的体制是最大的障碍;文化市场开放度太小是最终的原因。我们已经大致构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农村和国企的改革已经给出了明白的结论。问题是我们必须坚定地继续走下去,必须把市场经济的模式不失时机地推广到更重要的社会经济部门里去,比如金融业和文化产业;经济结构内部尚存的“双轨制”弊端已经阻碍了全局的健康发展,甚至就是酿成社会动荡的渊源。
事实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的国策。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已经明确地为其定了性。现在的问题只是这些政策如何可以得到具体地落实。市场化是改革的基本取向。所谓市场化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开放市场;二是打造市场微观主体。而近30年改革的经验表明,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不开放市场,旧体制下的生产单位就不会认真地转换机制,无法脱胎换骨。文化体制改革恐怕也无法回避这样的进程。我们实行行政垄断的时间长了,国企没有在市场条件下进行竞争的能力,所以我们希望市场开放之前给国企留一些“试水”的时间,国企毕竟是国有资产。但事实上,不面对市场,旧体制下的经济组织不可能主动调整,反而会在个人利益驱动下,利用转型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改革会有成本,但这个成本不应该太大。因为这个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制度腐败的温床。
从已经有限开放市场的一些文化领域看,中国人的原创能力并不差。美术品无论高端还是低端都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电影和艺术表演在国际上也有精彩展示;软件及网络业拥有一批具国际水准的公司;问题是我们是否让我们的文化产业也与传统制造业一样,成为完全的“世界工厂”。如果是这样,他们的生产标准势必是国际化的,而不是民族化的;作为文化多样性之一部分的中国文化的传承就会成为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打开国内文化市场,让中国人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问题可以这样表述:作为中国人,他是不是不仅应该有在中国的文化消费权,也有在这里的文化生产权、传播权。这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而国内文化产业能否做大做强也依赖于这个目标的实现。相信与前30来年的改革一样,一旦文化市场开放并不断予以规范,各类与我国居民文化需求相符的产品和服务会迅速增加;在形成买方市场之后,产品、服务的质量逐步提高,价格相对走低。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幸福感增加。
三、文化体制改革起步的方式宜于调整
自2000年起,文化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以“试点”的方式在国内一些地区、行业和企事业单位慢慢展开。应该说,通过近几年的试点,对于如何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人们有了一些认识,尤其是对于旧体制的弊病有了更多的认识。但是一些所谓改革举措却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例如可以说是改革最大举措的“集团化”试点几乎没有取得成功的经验。在行业垄断局面不改变的情况下,一些不彻底的改制导致了过度的商业化和公共服务责任的放弃。
问题出在哪里?尖锐一些讲,也许我们应该思考“试点”这种方式本身。人们说我们有中国国情,“试点”是国情的要求,不能不这么做。对于这种说法所有可能的含义,正面的或负面的,我都可以同意。今后似乎也不能完全避免。但像近几年所进行的这种“试点”方式似乎弊多利少。首先,市场开放应该公正,任何一个市场领域的开放应该是对所有境内居民同时开放。而现在的这种方式,一是让一部分经营者提前入场,导致不公平竞争;二是由此导致普遍追求提前入场,甚至不惜贿赂守门人,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因此,今后的“试点”方式仍需要重新思考。
也有人强调文化体制改革与此前各种改革不同的特殊性,他们不是指文化产品具有不同于商品属性的价值属性,而是说它们有意识形态属性。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性是内容放开的问题。文化生产的权利就是文化表达和传播的权利。对于市场上的文化内容需要监管和规范,而在改革之初就是一个逐步放开的问题。文化内容开放的试点就是分时间场合、按意识形态属性强弱等标准对所有的经营者试探性、同时开放的尝试。
这种内容开放有没有风险?显然有。但这是无法回避的。我们不能让在“战时状态”的政策永久化。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公共舆论和公共批评,不能没有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表达。
如果说文化体制改革与以前的农村或国企改革有什么不同,那么就是它不是在一种危机的状态下发动的。以前改革是由于没饭吃,由于要破产而被迫进行的。今天,我们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财政有极大的好转。但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的内驱力反而越小。加之各文化部门垄断利益很大,他们并不急于改变现状,甚至更愿意脚踩两只船,保住既得利益,争夺新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部门更有夸大文化体制改革和内容市场开放风险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公约》制定产生的机遇很可能会在磋砣中失去。
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要转变,文化体制改革也面临一个新的起点。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开放市场,是内容开放。无论如何分阶段分步骤,首先是要有一个时间表。这是面对机遇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