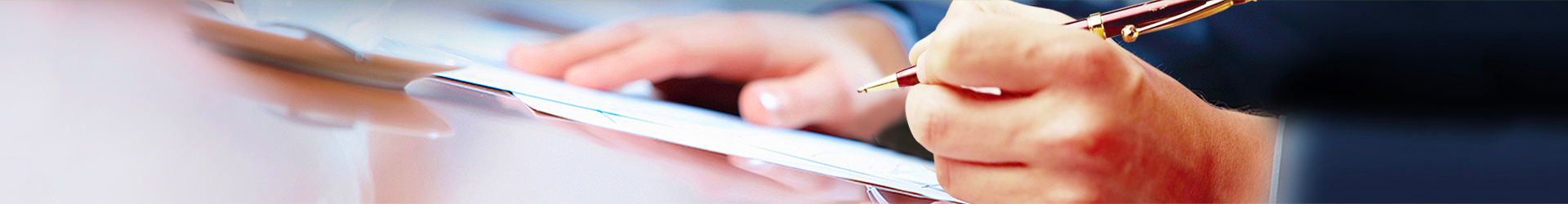
为运用《公约》这一政策工具做好准备
——出席《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政府间委员会08年6月特别会议的汇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哲学所 章建刚
2005年10月,《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33届教科文大会获得通过;2007年3月正式生效。2007年6月,《公约》第一届缔约方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政府间委员会,即它在教科文组织中的工作机构;中国成为了这个政府间委员会的第一批成员。这样,《公约》制定所引领的国际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将其宣言变成现实。大会决定由其选出的政府间委员会首先着手拟定一份《公约》实施操作指南,并最终交由2009年举行的第二届缔约方大会审议。
2007年12月,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第一次政府间委员会会议正式投入了《公约》“操作指南”的制定。“指南”是《公约》认定的原则的具体化。但是渥太华会议并不能一次完成“操作指南”的全部起草工作,只是就一些基本原则取得了共识,于是决定进行进一步筹备,在2008年6月加开一次政府间委员会的特别会议继续这些与“实施操作指南”相关的工作。由于我参加过《公约》起草过程的两次会议,也由于本次操作指南中涉及对公民社会的概念设定等理论性较强的内容,我受邀参与由文化部牵头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与会工作。
政府间委员会各成员国在本次会议较为具体地、逐段逐句地讨论了三个文件草案,即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的政策措施部分(涉及《公约》第7、8、17条内容)、伙伴关系的概念和模式(涉及《公约》第15条)、公民社会的作用和参与(涉及《公约》第11条及相关条款)的草稿;较为原则地对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使用的操作指南相关草案进行了讨论;还决定委托一些专家为《公约》16条即与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相关条款进行操作指南的文案准备。
会议按时间表完成了各项讨论,形成了相关的临时文件交今年12月举行的第二次政府间委员会正式采纳。应该说讨论还是较为富有成效的,讨论的气氛也是融洽的。但我也较强烈地感受到这个讨论环境与《公约》起草时的环境有较大的不同。《公约》起草时,参与的成员国很多,第三世界代表多,意见集中,常可形成绝对多数;同时在保护文化多样性问题上持反对意见的美国及少数盟友代表团在场;加之欧盟当时特别强调以一个声音说话,因此欧盟特别是法国的会上动作不是很突出。而这次会议上,未加入《公约》的美国仅作为观察员在场,而欧盟国家和法语国家在政府间委员会里席位较多,法国左右手相牵,很能主导会场形势。反之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等的声音相对较弱。尤其是在会议召开后,欧盟(主要是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在圣卢西亚一份修改稿基础上推出一份新的文案,主席(加拿大人)也同意以新的文案为讨论基础,使得中、印、巴等国感到有些措手不及。看来政府间委员会将是欧盟的“主场”,而我们与欧盟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毕竟有一些差别,因此中国代表团参与今后的会议还应有更充分的思想及文案准备。
当然从本次会议形成的各项文案上看,法国、加拿大或欧盟国家倒也没有因其优势地位而夹带私货,总体上是严格遵循了《公约》及其各项条款的原则要求;他们的文案主要是对原专家起草文案的“书卷气”有所更动。应该说,教科文秘书处和上一次政府间委员会对本次会议的筹备工作进行了较充分的准备。不仅对相关文案进行了认真的撰写,还约请专家提供了相关的参考文献。如与“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措施”相关,提供了“欧洲国家文化政策”和“拉美国家文化政策”两篇专家报告;与“伙伴关系”内容相关,提供了一篇关于伙伴关系生成的一般程序的文献;关于《公约》第8条所述“文化多样性濒危或受到威胁”,提供了澳大利亚专家思罗斯比的解释性文献等。应该说,这并不专门是为了向发展中国家展示经验,或为相关文案提供说明事例,而是力图显示出未来在保护文化多样性上开展国际合作的复杂性及可能面对的挑战;毕竟,文化间的交往更多涉及制度差异。
参加了会议的讨论,我觉得总体上说,我国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权利得到了肯定和维护;各种案文也不对我国的政策或安全构成冲突。应该说,《公约》这个为各国境内及国际间促进各自文化发展和多样性状况改善的政策工具已经是越来越锋利了。但有几个问题是值得今后特别关注、应充分前瞻的。缺少这些准备,也许这件利器就只是一件摆设。
首先,在与文化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政策措施方面,目前的文本已经提出了“价值链”的问题,即文化表达从原创、生产、传播、销售到获得享有的全过程,每个环节都应有相应的政策措施,而且这些措施通常说都是公共政策,都是为了对市场规则予以补充。这明显展示了欧盟在文化竞争中欲以公共政策尤其公共财政与美国文化产业抗衡、抵制高速经济全球化的意图及前沿所在,对我们将来制订尤其是细化文化政策有所裨益。但同时我们更应该从中意识到,欧洲各国在文化原创、生产能力和政策体系上都是较为充分的,只是由于语言及市场人口的限制,在产品针对市场销售的“临门一脚”上难以突破。他们能对价值链的观察这么细正是因为他们的各项基础已较为完备。而我们这个发展中和正在改革转型的国家,在文化原创、生产能力和政策体系方面都还有明显的差距,因此我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考虑相关政策措施,以及进行操作指南制定时,还应有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谋划。
其次是在伙伴关系构建方面。目前的《公约》原则上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予以优惠,在《公约》和“实施操作指南”中也充分照顾到发展中国家对主权问题的关切,甚至已经肯定伙伴关系只能由发展中国家发起,并根据其自身进行的文化多样性状况及需求评估,自主选择合作伙伴,但这最终将是以文化产品贸易及国家生产能力为目标的双边或多边合作,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建立在国家间以公共财政支持的文化交流或援助项目。我们从现在起就应该构想、选择合适的项目。
第三,《公约》似乎特别肯定了“公民社会”在相关工作中的作用和参与,尤其是《公约》制定至今各次会议上都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在场,他们对其中的机会已跃跃欲试了。从现代社会的角度说,公民社会对各项公共服务的参与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西方各国,要约束政府的规模就要有公民社会的充分发展,今天西方的公民社会更是抵制经济高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因此联合国机构如教科文组织当然也希望利用各种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推进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事业。但我国目前在公民社会的制度建设方面相对滞后,我们也不能因此在教科文组织及其《公约》谈判中抵制相关内容,可以做的只能是加速国内的体制改革和政策配套。对于国际上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即通常所说的非政府组织(NGO),尤其是与教科文及其《公约》实施有较固定关系的NGO需要谨慎、细致地研判其行动意图,对向他们赋权的条文尤其需要谨慎(当然西方各国政府也不会听任他们“夺权”或取得特权)。一般说,他们的成员有两种:一种是行业协会(如文化多样性国际联盟);另一种是文化人组织(如文化多样性国际网络即INCD)。前者往往对经济全球化有抵制,但因此也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有不满;后者要求文化发展,但也会对自由表达、人权问题有较高的标准。一般说,他们对知识产权都有维护的高要求。同时他们的成员往往是一批专家,具有各种经营管理和政策咨询的特长,因此他们会首先希望取得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的使用权,甚至是垄断性的、排他性的使用权。这一点尤其需要关注。我们应该注意在合作中动员我们的专家参与,以掌握项目的主动权。
参与教科文组织及与《公约》有关的外交活动使我有一种切身体会,即随着经济的壮大,中国人正在外交方面变得更加主动:从被动加入各种国际公约到主动参与公约的制定,但这种变化还不充分。我们现在的参与更多是主动的预防,即防止国际法文书中出现与国内政策不协调的内容。我们还应该从主动预防发展到对国家利益的自觉获取。欧盟的外交经验显然丰富,随着《公约》的落实,那些道义上的主张正逐一变成经济利益。因此我们也要学习西方人,不仅是把联合国及其机构当成论坛,而且要会把道德原则和现实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了不让《公约》这一政策工具闲置,我愿抛砖引玉,做一些后续行动的设想。《公约》最终会通过基金使用机制变成项目。我国作为缔约方自愿捐款,同时也就有了使用基金的权利。我们的文化发展并不依赖基金,但在中国崛起、希望获得更多文化软实力的今天,我们应该利用《公约》及其基金做几个示范项目,在联合国机构和世界文化发展中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我们可以设想分别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利用基金与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政策调研或比较研究,为国内文化政策发展及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在那里找到一些有市场前景的文化产品通过生产能力培养、人员培训、企业孵化和市场开拓将其推向国际并介绍到国内,从而丰富国际与国内的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接受的多样性。如果国内与文化相关的各个部委(如广电部、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也能前瞻性地设计出几个政策允许的或改革导向的国际文化合作项目,对于落实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中国和平外交的形象等等,都会是有相当益处的。如果这些设计或建议较为成熟,并能提前让中国代表团了解,那么在未来的会议及文件起草中我们就会更有目的地将相关的国际政策环境打造得更好,使我国的文化发展更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