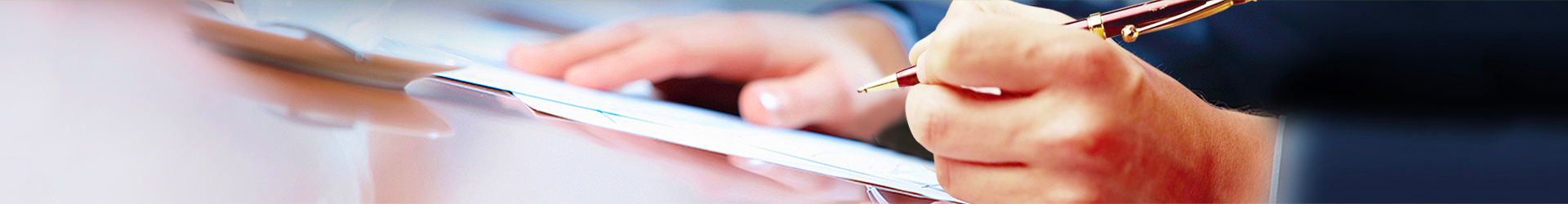
“优惠待遇”将成为2005年《公约》进入实操的关键
——参加2008年12月政府间委员会第二次常会的简要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哲学所 章建刚
2008年12月8-12日,《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现教科文组织中通常简称“2005年《公约》”)按计划举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政府间委员会”(2007年选举产生,参见我上次参加特别会议会的报告“为运用《公约》这一政策工具做好准备”)第二次常会。会议按事先安排,分别审议了有关“操作指南”的四个文件:“(与12条相关的)促进国际合作”、“(与13条相关的)将文化整合进可持续发展”、“(与14条相关的)为发展而合作”以及“(与18条相关的)文化多样性国际基金资源的使用”。会议还请有关专家就(与16条相关的)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的问题研究进行了简要报告。我感到,与08年6月政府间委员会特别会议相比,本次会议的气氛更加务实,协商的气氛更浓,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与此同时,也让人更多地感受到《公约》实施日益临近时各方的谨慎和试探。
应该说,《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公约》是一项很重要的国际公约,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会占一席之地。但它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相比,其具体目标与对象更难把握,文化多样性是一种状态,怎样是多怎样是少很难作定量描述;多了或者少了以后结果优劣也很难作简单评价。并且因此,与2005年《公约》相关的项目、合作、基金使用的成果评价都更为复杂。这时各缔约方都意识到,一个良好的国际公约必须与已有的其他国际公约互不冲突;同时,无论有多少单方面的优惠待遇或“倾斜”安排,最终都必须能惠及各方,实现共赢!事实上,这在存在着不同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宗教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间本不是很容易实现的事;而在制度安排实施及可能出现矛盾之前让规则设计得合理、周密更是极为重要的步骤。
尽管欧盟国家在《公约》进程的推动上始终居主导地位,但似乎他们并不企图通过《公约》框架谋取什么经济利益,相反对发展中国家予以某种优惠是他们的重要关切。发展中国家在政府间委员会的代表主要是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与圣卢西亚等。但印度似乎更关注《公约》执行过程中的程序公正;而巴西明显希望拓展《公约》受益人的范畴,将对各种弱势群体的扶助纳入其中。这当然都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参与,但对《公约》事业的实质影响并不太大。
中国代表团一直在会前有较为认真的准备,文化部牵头的部际协调机制(包括外交部、商务部、广电部、新闻出版总署、知识产权局及社科院等单位)有预案和案文准备。《公约》制订阶段的工作始终把握住对主权原则的强调,和对我现行国内政策的衔接,因此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发展状况良好。同时,我们一直注重通过《公约》伸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希望在“操作指南”的制定中将我方的国家利益体现进去。本次会议当中,我代表团就发达国家应在信息技术转让方面优惠发展中国家的内容明确提出,并被相关草案采纳。这是对《公约》事业的实质性和建设性的参与,树立了我国政府在教科文组织中的正面形象。
回顾《公约》制定与推进的全过程,其贯彻、实施,包括“文化多样性基金”使用的基本思路似乎是这样的:首先,文化多样性状况与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要将文化维度整合到各国的发展战略中去。其次,发展要求合作,合作为了发展。这里说的合作特指国际合作;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再次,这些合作应该有商业合作,同时也不仅是商业合作。最后,考虑到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这些国际合作应不完全是对等的,而是包含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本次会议有一个小小的插曲。第一天上午的会议讨论“国际合作”草案。其间一些欧盟国家和法语国家集团提出,国际合作也应包括“北北合作”的形式。但这一发言马上受到发展中国家尤其印度、巴西等的反对。反对意见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一直就存在,《公约》操作指南不必再次作排列组合式的表述;因为这样做只会削弱、干扰了对发展中国家予以优惠待遇的明确倾向,因而削弱《公约》的作用。的确,《公约》文本中已经多处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求应得到满足;文本中已写明了进行文化合作对减贫、缩小贫富差别等的意义。最后,会议决定取消对第12条“国际合作”再作“操作指南”。回到起点:第一个半天的会议竟是这样的结果。事实上,本次会议讨论的几个草案都还是一些原则或建议,与未进入实质性讨论的“优惠待遇”问题相比,重要性要低得多。
“优惠待遇”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人们不能设想发达国家拿出大把的钱向发展中国家分发。
各方原来均很关注的《公约》第20条,即“与其他法律文书的关系”,现在似乎并没有太多国际法方面的横向关联问题,因为欧盟专家将WTO中“特殊与区别对待”条款找出来,说明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制度安排。但是,什么才算“优惠”,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市场讲究公平交易,公平体现为等价交换,而公平价格的形成取决于双方“合意”。那么,优惠待遇是要求只有一方合意的交换吗?对方凭什么要接受这种合作建议呢?更何况,没有市场价格形不成,什么是优惠也说不清。因此,优惠待遇只能是有限度的(让步),而且必然会有长远利益作为施惠方的动机支撑。其次,施惠方还要关注这种有限的、符合长远利益的“好处”会不会在受惠方的使用过程中被改变用途或目的呢;如果要不被改变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进行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呢,等等。这些考虑都是应该得到理解的。
因此,政府间委员会对“优惠待遇”条款的操作指南形成极为谨慎。本次会议并不直接讨论相关“操作指南”草案,而是分发了六个专家报告,并说明将来实施还会有一个“领航阶段”(pilot phase,相当于我们说的“试点阶段”)。这些统一体例的报告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分别对“优惠待遇”的概念含义加以说明,说明其是什么或包括什么,以及不是什么或不包括什么。接下来,这些报告主要检索了各国的相关法律制度环境及目前已签署的各种国际合作条约的状况。毕竟未来的合作很可能是不同社会制度间的对接。
在本次会议刚刚结束之后,“亚欧会议”在越南河内组织“论坛”,其主题是“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分享亚欧经验”。从会议的分组议题看,其主办方(主要是欧盟)关注的仍是同样的问题。三个分议题分别是“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多样性公共政策”、“亚欧内部与之间的文化交流再平衡”和“为发展共同行动”。尔后,教科文秘书处向各缔约国分发了有关“优惠待遇”的调查问卷。可见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公约》继续推进的关键环节,也会是下一次政府间委员会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
因此,我们这个部际协调机制应将注意力转到这个问题上来。这次的调查问卷也可以被看作是欧盟的“寻价”方式。我们应该将自己的要求明确而适当地开列出来:如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开放市场(此前《公约》的相关文字之说“要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提供方便”);要为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家及文化从业人员进入发达国家提供入境方便,等等。因为这样的条件都是单方面的,让我们提我们就这么提,“出价”本来可以高一些。发达国家在优惠待遇的语镜下反而不好要求我们对等开放。
通过参加这两次政府间委员会会议,我对欧盟国家在《公约》框架下的战略目标也有一些新的揣测,似乎除了可能进行一些不完全对等的文化贸易(不对等的贸易总是难以持续的),开展一些文化交流,似乎他们也在希望“示范”某种有关人类发展的“欧洲模式”。尤其这样的“欧洲模式”与我国当前努力寻求的“科学发展”似有一些相似之处。是不是这样,尚需拭目以待!